明代晁瑮《寶文堂書目》素被視作中國古代話本小說的寶庫。學界長期流行一個“常識”,即認為該書目中著錄了“簡稱”,如《柳耆卿記》《孔淑芳記》《杜麗娘記》分別是《柳耆卿詩酒玩江樓記》《孔淑芳雙魚扇墜記》《杜麗娘慕色還魂》等話本小說的“簡稱”。然而新文獻的發現與細致的文本內證表明,此“簡稱說”實為一代學人在史料局限下的或然性推定,有必要予以匡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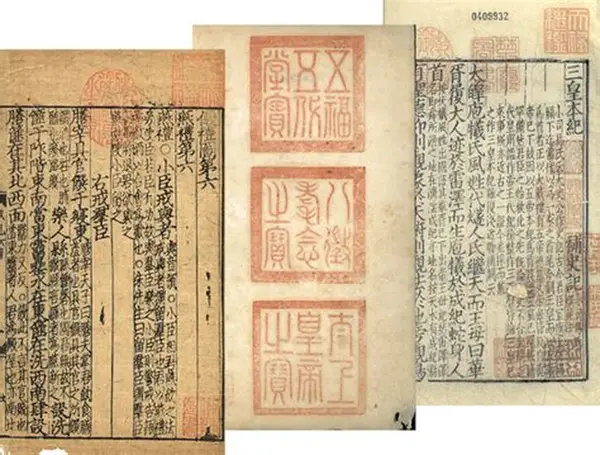
自1920年代前輩學者開創中國古代小說目錄學研究以來,《寶文堂書目》的地位便舉足輕重。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1931)等首次系統考證并推定了《寶文堂書目》中諸多篇目的性質,篳路藍縷;譚正璧《宋元話本存佚綜考》(1941)和《寶文堂藏宋元明人話本考》(1942)、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1980)等繼之深化,功不可沒。為將篇目進入古代小說目錄學體系和納入小說史源流,他們創立并強化了“簡稱說”(或類似說法)。前輩學者在資料匱乏的情境下多持“存(?)”“疑”“可能”等審慎態度,但后期學者論述時則漸多“又名”“亦名”“當”“即”“當即”等必然性論斷,且被學界接受, 固化為確鑿的定論。然予以細究,“簡稱說”自誕生之初便存在三重缺陷。
其一,證據的或然性與循環論證。“簡稱說”大多建立在名稱相似與情節對應的或然性推理之上。因《清平山堂話本》有話本《柳耆卿詩酒玩江樓記》,便推定《寶文堂書目》中的《柳耆卿記》為其簡稱。然而此說缺失版本學證據支撐。相反,《清平山堂話本》的實物版心簡題為《江樓記》,綠天館主人《古今小說敘》簡稱《玩江樓》,均與《柳耆卿記》無涉。而《柳耆卿記》之名,反與宋羅燁《醉翁談錄》丙集卷二《花衢實錄》中《柳屯田耆卿》的總名高度吻合,而且總名之下尚有《耆卿譏張生戀妓》《三妓挾耆作詞》等子目。《寶文堂書目》著錄的《柳耆卿記》,更可能是指向總名類文言故事集,而非話本的簡稱。
其二,邏輯的先入為主與體裁誤判。在二十世紀“白話文學為中心”的研究范式下,學者們對《寶文堂書目》中“其名目近似話本題目者”往往下意識地預判為話本,而忽略了這些篇名本身作為文言小說存在的可能性。《話本敘錄》(2001)多以《寶文堂書目》著錄的名稱作為“書名”,以“又名”“亦名”關聯現存話本小說;至《中國古代小說總目》(2004)將《杜麗娘記》《孔淑芳記》等直接納入“白話卷”,是這一預判未經審慎考辨的集中體現。《寶文堂書目》明確可判定為文言小說或小說集的著錄,達30多種,其中包括《鶯鶯傳》《離魂記》《紅線傳》等唐傳奇,以及《嬌紅記》《懷春雅集》等明代中篇傳奇小說。“某某傳”或“某某記”正是文言小說最常見的命名方式。因為有現存話本小說《孔淑芳雙魚扇墜記》《杜麗娘慕色還魂》,而將《孔淑芳記》《杜麗娘記》等少數篇目判定其為話本“簡稱”而非文言小說,在邏輯上難以自洽,實質上還是一種選擇性闡釋,應首先將其置于《寶文堂書目》本身的整體著錄慣例中加以考量。
其三,對書目性質與著錄通則的誤判。《寶文堂書目》并非一部精心構建學術體系的分類目錄,更多可能是晁氏家族清查自家藏書的“賬簿”。(參見溫慶新《晁瑮〈寶文堂書目〉的編纂特點》)四庫館臣批評《寶文堂書目》“編次無法,類目叢雜”,事實上屬于精英視角,后世學者多援引此說,卻罕有深究其“無法”和“叢雜”背后的真實原因,那就是《寶文堂書目》作為私家藏書賬簿的原始性與實用性。晁氏家族直接抄錄藏書原名,并無意識區分文言、白話的文體畛域。
更重要的是,從目錄學的通則來看,“簡稱”現象并非普遍。考察古代著作,題名的簡稱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雜劇、傳奇有以“正名”末三字作簡稱的慣例;二是單部著作由于卷首、卷尾、書腰等不同位置而題名有詳略之別;三是《醉翁談錄》等例舉話本篇目時出于韻文或修辭需要而做出減省。但在書目著錄層面,將一部著作著錄“簡稱”而非全名,除學界強加于《寶文堂書目》的“簡稱說”外,筆者尚未得見類似情況。《寶文堂書目》既然著錄《新刻古文會編》《新刊諸癥辨疑》《新校續衛生方》《新增急救易方》《增續韻府群玉》時,“新”“增續”等前綴詞一字未減,那么還有必要采用“簡稱”嗎?“樂府”類《降六賊伏龍虎太平仙記》《張繼宗怒殺煙花女記》等字數更多,都沒有使用簡稱,為何單單是“子雜”類對話本使用“簡稱”呢?如果真的采用“簡稱”著錄,也難與其“賬簿”式的著錄動機契合。《寶文堂書目》存在大量“重復”著錄,其成因復雜:或為藏書復本,或為同書不同版次,或為同主題而書名略異,或同書名但不同文體。而“同書名但不同文體”尤為關鍵。被舊說認定為“疑是名近同書”者十三種二十七本,皆當作二書看待,而不是著錄失誤。若晁瑮同時藏有文言《孔淑芳記》與話本《孔淑芳雙魚扇墜傳》,其最可能的結果是兩書并錄,而非要將一名充作另一名的簡稱。“樂府”類同時著錄《司馬相如題橋記》和《漢相如題橋記》,亦當是二書,而非簡稱。
于此可見,“簡稱說”并非憑空產生,其形成、固化乃至成為“常識”,是中國古代小說研究草創時期特定學術生態的產物,其根基并非無可動搖。
關鍵性新材料《稗家粹編》的發現與研究,對“簡稱說”的根基而言,不啻釜底抽薪。
明萬歷二十二年(1594)胡文煥序刻的《稗家粹編》,卷六收錄的《孔淑芳記》《杜麗娘記》,皆為傳奇體文言小說。它確鑿地證明了一個事實:《孔淑芳記》《杜麗娘記》完全可以而且也確實是兩篇文言小說。因此,《寶文堂書目》的著錄,首先最應指向的就是晁瑮書架上與《稗家粹編》所收文本性質相同的文言小說。這個重要物證使得“簡稱說”失去立足之地。相較于需要多重推演的“簡稱”假定,晁瑮著錄的就是家藏的文言小說,這一解釋無疑更為直接、合理與經濟。
顛覆“簡稱說”的更有力的證據,來自文本肌理的細讀及其生成過程的還原。筆者發現,《孔淑芳雙魚扇墜傳》的成書極為粗糙,但其文本生成路徑清晰可辨:以《西湖游覽志馀》卷二十六(181字)和《孔淑芳記》(500字)的故事框架為敘事主干,而在文字層面上則大量模仿、因襲《剪燈新話》中的《牡丹燈記》《滕穆醉游聚景園記》等篇。其文本中出現的有違生活常理、當時情境、語言邏輯、文氣連貫等眾多紕漏,正是改編者水平不高、在機械模仿和生硬拼接前代文本時顧此失彼所留下的鐵證。(詳參《明清小說研究》2006年第3期)這就構成了一個無可辯駁的、具有絕對時序意義的證據鏈:相對文言傳奇體《孔淑芳記》而言,話本小說《孔淑芳雙魚扇墜傳》無疑是一個晚出的、次生的、拼湊而成的改編本。話本《杜麗娘慕色還魂》的開場詩(“閑向書齋覽古今,罕聞杜女再還魂。聊將昔日風流事,編作新文厲后人”),無異于是改編者的創作聲明:在“書齋”中閱覽“昔日”舊事《杜麗娘記》,而后將其“編作”成“新文”。其文本內部存在的大量疏失與前后矛盾,正是改編者在敷衍擴寫過程中,受制于藍本框架而顧此失彼、無力圓融所留下的明證。若反過來認為文言傳奇體《杜麗娘記》是在話本小說體《杜麗娘慕色還魂》的基礎上“后出轉精”,則根本無法解釋:為何話本會開頭自稱“編作新文”?相反,用文言源本到話本劣改來解釋,則豁然貫通。《孔淑芳記》《杜麗娘記》這兩個案例,猶如雙核互證,共同指向一個無可爭議的結論:現存的話本乃是衍生性、次生的“流”,而《寶文堂書目》所著錄的文言小說,才是“源”。
基于上述新證據與內證分析,我們有必要對《寶文堂書目》的著錄性質及由此構建的明代小說史圖景進行根本性的重構與正名。
其一,徹底摒棄“簡稱說”的思維定式,回歸書目的原始性質。尊重《寶文堂書目》作為私家藏書賬簿的根本屬性。晁瑮著錄《某某記》,意味著他當時收藏并清點的就是一本題名為《某某記》的書。《稗家粹編》的發現已證明,這類名稱的著作完全有可能而且常常就是文言小說。因此,在無確鑿反證情況下,應首先將其認定為文言體,而非預先假定為某話本的簡稱。
其二,充分認識其著錄體例的復雜性。晁氏書目的一大特色,即著錄了大量單篇作品。《合同文字記》《羊角哀鬼戰荊軻》等見于《六十家小說》,并分散著錄,這是“賬簿式”著錄的明證。一個更具重要的例證是,該書目著錄的《離魂記》《虬髯客傳》《霍小玉傳》《南岳魏夫人傳》等唐傳奇名作,與明代著名文言小說選集《虞初志》在篇目和著錄順序上非常接近。晁瑮收藏并清點的,很可能正是《虞初志》或與之類似的文言小說總集,而他采取的著錄方式,正是按篇名登記入賬。《寶文堂書目》中的著錄,并非獨立單行的話本,而是某部文言小說總集中的一篇。這對于《柳耆卿記》《孔淑芳記》《杜麗娘記》等而言,意味著它們完全可能是來源于某部已佚文言小說集或選本中的篇目,其性質當為文言小說,與話本小說的“簡稱”南轅北轍。
其三,應確立“文言源本→話本改編”的生成模型,以取代舊有的“簡稱”對應關系。明代的小說生態是文白交織、相互影響的動態系統。許多話本小說并非空穴來風、憑空原創,其標準且常見的創作模式,正是對現有文言小說進行擴寫或敷衍,以適應市井說書或下層文人與市民的閱讀需求。正如《孔淑芳記》《杜麗娘記》所清晰展示的,文言小說提供了最核心的故事框架、人物原型,而話本則是在此基礎上敷衍成文。其成敗,全系于改編者的才力,或點鐵成金,或畫虎類犬,留下較多紕漏。這一生成模型遠比靜態、簡單的“簡稱說”更能合理解釋文本之間復雜的互文關系與藝術質量的差異。
其四,亟待對《寶文堂書目》著錄小說進行系統性的重新認定與甄別。筆者曾經提出“認定—辨體—區分版本”的三步法,以便對書目中的小說篇目進行重審。對《柳耆卿記》,應充分考慮其指向《醉翁談錄·花衢實錄》之類文言軼事集的可能性。對《李亞仙記》,則必須正視其有話本體《李亞仙不負鄭元和》《李亞仙記》、傳奇體《鄭元和嫖遇李亞仙記》等多種版本并存的現實,細究晁氏所藏究竟是為何本。對于《清平山堂話本》本《風月相思》、熊龍峰刻本《馮伯玉風月相思》、《國色天香》本《風月相思》三種故事大致相同但文字有異者,也當如此。這項工作的目的,絕非否定前輩學者的奠基性貢獻,而是以新發現的材料、更精密的文本分析方法及對書目體例的準確理解,推動學術研究向著更貼近歷史真相的方向不斷發展與深化。
總之,文言傳奇體《孔淑芳記》與《杜麗娘記》的重新發現,以及由此出發對相應話本進行的文本生成學分析,有利于解開長期束縛學界的“簡稱說”的枷鎖。它揭示了一個被長期誤解的文學史實:晁瑮的書架家藏,多為文言小說。質疑和顛覆“簡稱說”,不僅是對《孔淑芳記》《杜麗娘記》等具體篇目的正本清源,更是對明代小說,尤其是話本小說生成與傳播史的修正。它使我們得以跳出“話本中心論”的窠臼,重新審視并充分肯定文言小說系統在明代小說生態中的基礎與源頭的作用,從而最終深描出更為復雜、真實、生動且符合歷史本來面貌的明代小說圖景。
來源:光明網






 掃一掃分享本頁
掃一掃分享本頁



















